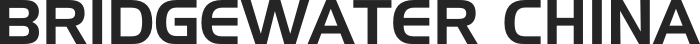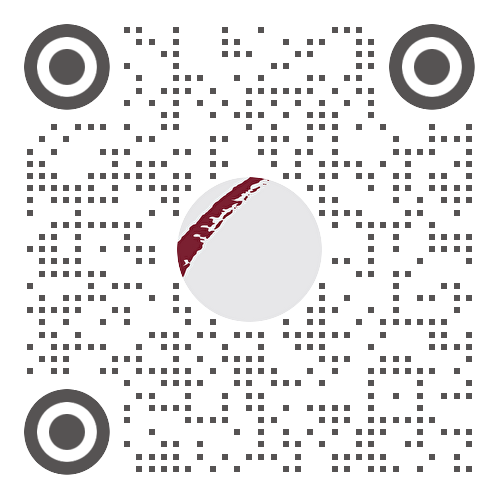2022年初,美国和欧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实施的刺激措施初见成效。第三货币政策发挥了作用,使这些国家的经济从崩溃转向腾飞,实现了极高的名义经济增速和名义支出,收入增速超过供给增速,引发通胀。这些政策还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拉动资产价格走高,使人们手中和金融系统中还保有流动性。
各国央行,特别是美联储,面临抉择:是以超过市场预期的速度收紧,还是冒着不断加剧的通胀压力变得根深蒂固的风险。俄乌冲突加剧了本就糟糕的通胀形势。美联储选择了快速的紧缩政策。
2022年货币紧缩政策实施的速度和力度是历史上最为激进的。美联储和其他央行采取的每一项措施可以说都成为了影响市场的唯一因素。几乎所有资产的走势都符合其与实际利率之间的关系。最终,市场预期反应了实际收益率的走势。但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尚未预期我们认为紧缩措施极有可能造成的其他影响。
紧缩对市场造成巨大冲击,且波及范围很广。然而,紧缩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尚未完全显现。这些影响即将来临。否则,未来将有必要继续实施紧缩,直至劳动力市场足够宽松,使得工资通胀降至可以持续实现通胀目标的水平。
要使得通胀率持续维持在2%左右的水平,一些变化必须出现。而市场却并未对其中的大多数变化作出预期。
- - 名义支出增速必须降低至3%-5%的区间,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通胀率在央行目标附近波动时,名义支出增速就是处于这种水平。不过,仅凭这一点不足以实现通胀目标。
- - 要想实现可持续的均衡,就需要名义支出增速处于这一区间,同时实际经济增速接近目标水平。这就要求工资通胀率降至1%至3%的区间,就像过去几十年那样。
- - 如果名义支出增速为3%到5%,工资通胀率接近2%,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这两个目标是有可能的;即实际GDP增速和产出达到潜力水平,通胀率接近2%的目标。
- - 但是,考虑到目前的起始点,恢复均衡状态将需要很长一段调整期,期间名义支出增速处于低位,实际经济增速为负值,失业率增加。
- - 简单来说,这意味着失业率至少上升2%,并在很长时间里保持该水平,以实现劳动力供需平衡,实际GDP降低2%,营业收入减少20%左右以带来足够规模的裁员。
通往均衡的道路
通常来说,经济体在均衡状态下运行得最好。政策制定者在运作良好时,会利用他们的工具推动经济体走向均衡。我们认为实现均衡需要三个必要条件:
- - 支出和产出与产能匹配
- - 债务增长与收入增长相匹配
- - 资产相对于现金的风险溢价处于正常水平
新冠疫情导致经济体运行严重失衡。为了应对,政策制定者实施了有助于拉动经济复苏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第三货币政策)。由于实施该政策的力度很大,持续时间很长,导致经济朝着另一方向失衡。因此,2022年进入了大规模紧缩周期,并且这一周期很可能会延续至2023年。
当前,实现均衡需要的条件都不存在。名义支出的规模明显超过劳动力的产出能力,从而造成通胀。降低支出很有必要,这最先带来的影响是实际经济增速下滑,即朝着另一个方向的失衡。利率仍明显低于名义支出增速,从而支撑信贷增长,进而在货币政策紧缩的情况下支持消费。倒挂的收益率曲线导致债券相对于现金不再提供风险溢价,而股票定价显示股票相对于债券的风险溢价也非常小。
政策工具的效力减弱,通往均衡的道路可能出现反复且波动性很大。通常来说,第一步是在经济增长强劲时通过紧缩抑制通胀。一旦经济增长被抑制、通胀呈下行走势,往往需要暂停紧缩,观察形势如何转变。暂停紧缩往往导致资产价格大幅上涨。这会支撑经济,降低通胀跌幅,因此有必要实施第二轮紧缩。这些暂停紧缩的做法往往还会导致货币贬值,从而加剧通胀压力,增加进一步实施紧缩的可能性。
在1970年代,大多数国家需要实施三轮紧缩。德国是个例外,因为该国在1970年代第一轮紧缩的力度就很大,足以使债券收益率和名义支出在1970年代早期(而非末期)出现下行走势。其他国家都是在1970年代末期才出现债券收益率和名义支出走低的趋势。
我们认为通向均衡最可能的道路是政策在很长时间里徘徊在紧缩(以抑制通胀)和宽松(以拉动经济增长)之间。关于接下来的走势,经济疲软时,央行将面临暂停紧缩的压力。考虑到从政策实施到经济增长发生变化以及从经济增长发生变化到通胀形势发生变化之间的时间差,央行做决定时,将无法确定紧缩力度是否已经足够或是过大。
其次可能的路径类似于1970年代德国的情况:持续实施的大规模紧缩带来严重的经济衰退,解决了劳动力失衡,使工资通胀以更快速度降低。
我们认为最不太可能出现的路径是当前的市场预期:经济立刻转向均衡,不会给经济或公司盈利造成太多冲击;加息在2023年3月左右触顶;短期利率在之后的两年里降低200个基点,并且不会导致通胀率再次上扬。
欧洲和英国面临与美国类似的情况,而且俄乌冲突及其对能源市场的影响以及对这些国家财政平衡的连锁反应导致它们面临的情况更复杂。通胀上扬,经济疲软,俄乌冲突造成的冲击使人们更难看到货币和信贷基本面对通胀的影响。迄今来看,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在紧缩周期中所处的位置落后于美国。这些国家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欧洲和英国离实现均衡更远,实现均衡的道路可能非常波折。
实现均衡需要通过恰当的形式使工资通胀率降低
在实现均衡的道路上,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是通胀率能否保持在2%。关于这一目标,工资通胀率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因为1)工资带来用于消费的收入,并且2)工资是公司最大的一项成本,影响着定价。因此,3)如果工资很高,消费者就有钱购买价格更高的商品、公司就有了据此涨价的动力。这种自我影响的相关性从本质上看具有自我强化性,直到因为某些原因而停止循环。
工资通胀已经呈上行走势。美国的工资通胀率上涨了5%左右,并且出现在各个行业。美国15个主要行业中,14个行业的工资通胀率都超过4%。这意味着即便商品通胀率跌至2%甚至更低,如果工资通胀率仍接近5%,总体通胀率将会朝着5%上扬。下图显示工资如何成为影响通胀率的最主要因素。除非工资走势发生变化,否则通胀率仍将扭转成与工资通胀率一样的水平。

那么,影响工资的因素是什么?简单来说,工资就是价格,即劳动力的价格。和任何价格一样,工资取决于追逐一定数量劳动力的资金数量相对于追逐资金的劳动力总量的情况。

我们可以通过名义GDP,也就是整个经济体支出的资金总额,反映出多少资金在追逐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如下图所示,名义支出增速是决定工资通胀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支出不高,人们就不可能获得高工资,反之亦然。(目前)名义支出水平过高,无法使通胀率保持在2%。为了使工资降至与2%通胀率相符合的水平,名义支出增速必须降至3%到5%左右,就像最近几十年通胀率接近2%时那样。这相当于我们去年支出增速的一半左右。

我们可以用失业率来反映追逐资金的劳动力总量。如下图所示,我们将实际失业率减去6%的水平作为长期失业率的大致中心点,并计算出失业率的平均水平和平均波动幅度。从中可以看出,失业率的水平和波动幅度(见图中红线,纵轴倒置)也是影响工资的重要因素。当前失业率同最低值相比有所回升,不过仍是拉动工资上涨的重要因素,其影响接近过去5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要想使这一影响因素转变为推动工资下行的因素,需要失业率至少上升2%,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维持,只有这样才能影响劳动力供需。历史上看,这大约持续了18个月左右。

如上图所示,目前,名义支出增速和失业率都给工资造成上行压力,而非下行压力。
在这些影响因素中,名义支出和工资之间的差异给失业率带来压力,因为从整个经济角度看,名义支出相对于工资的情况代表着公司利润率。其中的逻辑在于,为了推高失业率,名义支出必须相对于工资降低,即收入必须相对于成本降低,导致利润率降低,从而促使企业裁员。下图显示名义支出和工资之间的差异(数据取自上图)以及失业率的变化情况。纵观历史,要想使失业率显著上升,名义支出增速必须明显低于工资增速。近期的工资上涨得益于名义支出增速明显超过工资增速,拉动公司利润和招聘大幅增加。(目前)名义支出增速仍超过工资增速,因此失业率面临的上行压力并不大,除非名义支出增速明显低于5%。我们迄今实施的紧缩力度可能足以使名义支出增速在2023年明显低于5%。如果不是,央行将有必要加大紧缩力度,直至名义支出增速降至这一水平。

分析这一动态的另一个视角是公司盈利。其中的逻辑在于,以前从未出现过失业率大幅上涨时公司盈利没有降低的情况。公司盈利必须降低20%左右,才能引发足够规模的裁员,从而将失业率推高至足以拉动工资下降的水平。目前尚未出现这种情况。

对以上的关联及其带来的影响总结如下:
- - 工资是影响通胀率的重要因素,并且目前一直保持着5%左右的增速。要想使通胀率降至2%,工资增速需要降至2%左右。
- - 如果要降低工资通胀率,需要名义支出增速降低,失业率上扬,从而重新平衡资金和劳动力总量之间的关系(P=$/Q)。
- - 要想提高失业率,需要名义GDP增速大幅低于工资增速,进而导致公司利润率降低,使公司利润减少20%左右。
- - 此外,这些形势必须非常极端,且持续时间足够长,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劳动力供需平衡,实现2%的工资增速。以之前的情况为例,失业率需要上升2%并在持续18个月左右的时间。
我们目前距离这些形势的出现还很远。这说明我们在实现均衡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一过程中,央行面临许多艰难抉择,而且市场也会出现波动。
美元荒
由于美元是全球主要融资货币,美联储紧缩会对其他国家的国际收支造成巨大冲击。随着紧缩导致美元相对其他货币升值,外国美元借款者不得不将更多自己持有的贬值货币兑换成美元,以偿还债务。这导致美元相对于这些货币进一步升值。由于美元紧缩还造成全球经济增长和出口需求放缓,上述汇率动向往往在美元债务国国内经济增长疲弱、经常账户余额恶化的情况下出现。在这些国家,这种自我强化性周期经常升级为国际收支危机,成为又一个需要通过美元最终放宽、其他国家收紧政策和美元债务国经济增长放缓来解决的失衡。
美联储实施的大规模紧缩加剧了美元流动性从紧,也导致美元汇率达到长期以来的高位,经常账户出现严重赤字。这使得当前较高的资本流入水平成为保持美元稳定所需的盈亏平衡资本流入水平。因此,美元很容易受到美国经济走弱以及美国紧缩周期相对于其他国家出现扭转的影响。

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
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形势与西方国家当前面临的形势完全不同。为了应对新冠疫情,中国、日本和其他亚洲经济体选择采取社会措施,而不是大规模货币和财政刺激措施。因此,这些国家的名义支出增速目前明显更低且接近正常水平、通胀率处于或低于目标水平。需要注意的是,主要经济体的通胀形势存在这么大差异在当前来看是不寻常的。这说明西方国家出现通胀的根本原因是它们所实施的货币/财政刺激措施,而亚洲国家并非如此。这也有助于分析正在经历由货币政策引发的通胀的国家未来需要实施的紧缩力度。
美国、欧洲和英国必须实施大规模紧缩才能抑制通胀,而中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刺激经济。中国政策制定者没有受制于过高的通胀率,并且经济运行也处于潜力水平之下。然而,中国政策制定者也很克制,避免过度流动性和过度杠杆化“漫灌”整个体系。
通常来说,当前是放宽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时候。政策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同时中国还放宽了动态清零的限制性措施。政策制定者将稳经济置于首位,预计将2023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5%左右,同时还将坚定贯彻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这个原则。中国决策者的政策意图是通过加强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措施的协调来实现协同效应。理想情况下,这将拉动内需,同时针对中小企业,促进就业,增加供应,以实现关键领域的自给自足。此外,他们呼吁“大力吸引和充分利用外资”来支持其目标,并且自二十大闭幕以来就积极鼓励外资流入,继续放宽房地产市场,支持私有企业,承认市场因素的作用,推广国际商业惯例并加强法制。
当然,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是中美之间紧张局势和战略竞争带来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西方国家将生产从中国转移至其他国家的需求无疑将带来越来越大的影响,限制从西方国家向中国的技术转移也是如此。此外,一个更重要的风险因素是紧张局势可能演变成两国之间更严重的针对性措施。
本篇《桥水观察》撰写于2023-1-6
本刊由美国桥水投资公司(Bridgewater Associates, LP,简称“美国桥水”)或经其授权由桥水中国编辑发布,并归美国桥水所有,仅限于提供信息和教育的目的。本刊并不考虑任何阅读者的特定投资需求、目标或风险承受能力。此外,因客户投资限制、投资组合调整和交易成本等多种因素,桥水的实际投资有可能(并经常会)与本刊得出的结论不同。阅读者在作出任何投资决定之前,应当咨询各自的顾问,其中包括税务顾问。本刊并非出售或者邀请购买文中提及的证券或其他证券的要约。
未经美国桥水和桥水中国事先书面同意,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转发、转载、翻版、复制、刊登、发表、修改、仿制或引用本刊内容。
桥水研究部采用来自公开、非公开和内部渠道的数据和信息,包括来自桥水实际交易的数据。信息来源包括BCA、彭博财经社(Bloomberg Finance L.P.)、Bond Radar、Candeal、Calderwood、CBRE, Inc.、CEIC 数据有限公司(CEIC Data Company Ltd.)、柯拉鲁斯金融技术公司(Clarus Financial Technology)、加拿大会议委员会(Conference Board of Canada)、Consensus Economics Inc.、Corelogic, Inc.、Cornerstone Macro、Dealogic、DTCC Data Repository、Ecoanalitica、Empirica Research Partners、Entis(Axioma Qontigo)、EPFR Global、ESG Book、欧亚集团有限公司(Eurasia Group)、Evercore ISI、Factset 研究系统公司(Factset Research Systems)、《金融时报》有限公司(The Financial Times Limited)、美国金融业监管局(FINRA)、GaveKal研究公司(GaveKal Research Ltd.)、全球金融数据有限公司(Global Financial Data, Inc.)、《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哈沃分析有限公司(Haver Analytics, Inc.)、机构股东服务公司(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 Services)、加拿大投资基金学会(The Investment Funds Institute of Canada)、ICE Data、ICE Derived Data (UK)、投资公司协会(Investment Company Institute)、国际金融协会(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Finance)、摩根大通(JP Morgan)、JSTA 顾问公司(JSTA Advisors)、MarketAxess、 Medley 全球顾问公司(Medley Global Advisors)、Metals Focus Ltd、Moody’s ESG Solutions、MSCI有限公司、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养老金及投资研究中心(Pensions & Investments Research Center)、Refinitiv、 罗迪集团(Rhodium Group)、RP Data、鲁滨逊研究(Rubinson Research)、Rystad能源公司(Rysta Energy)、标普全球市场情报公司(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Sentix Gmbh、上海万得资讯有限公司(Shanghai Wind Information)、Sustainalytics、Swaps Monitor、Totem Macro、Tradeweb、联合国(United Nations)、美国商务部(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Verisk Maplecroft、Visible Alpha、Wells Bay、万得金融信息有限公司(Wind Financial Information LLC)、伍德麦肯兹有限公司(Wood Mackenzie Limited)、世界金属统计局(World Bureau of Metal Statistics)、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YieldBook。虽然桥水认为来自外部来源的信息是可靠的,但桥水不对其准确性承担责任。
本刊所含观点谨代表桥水在发布之日的观点。若有改变,恕不提前通知。桥水可能在本资料讨论的某个或多个投资头寸及/证券或衍生品种拥有重大金融利益。本刊撰写人所获的报酬取决于各种因素,包括工作质量和公司收入。